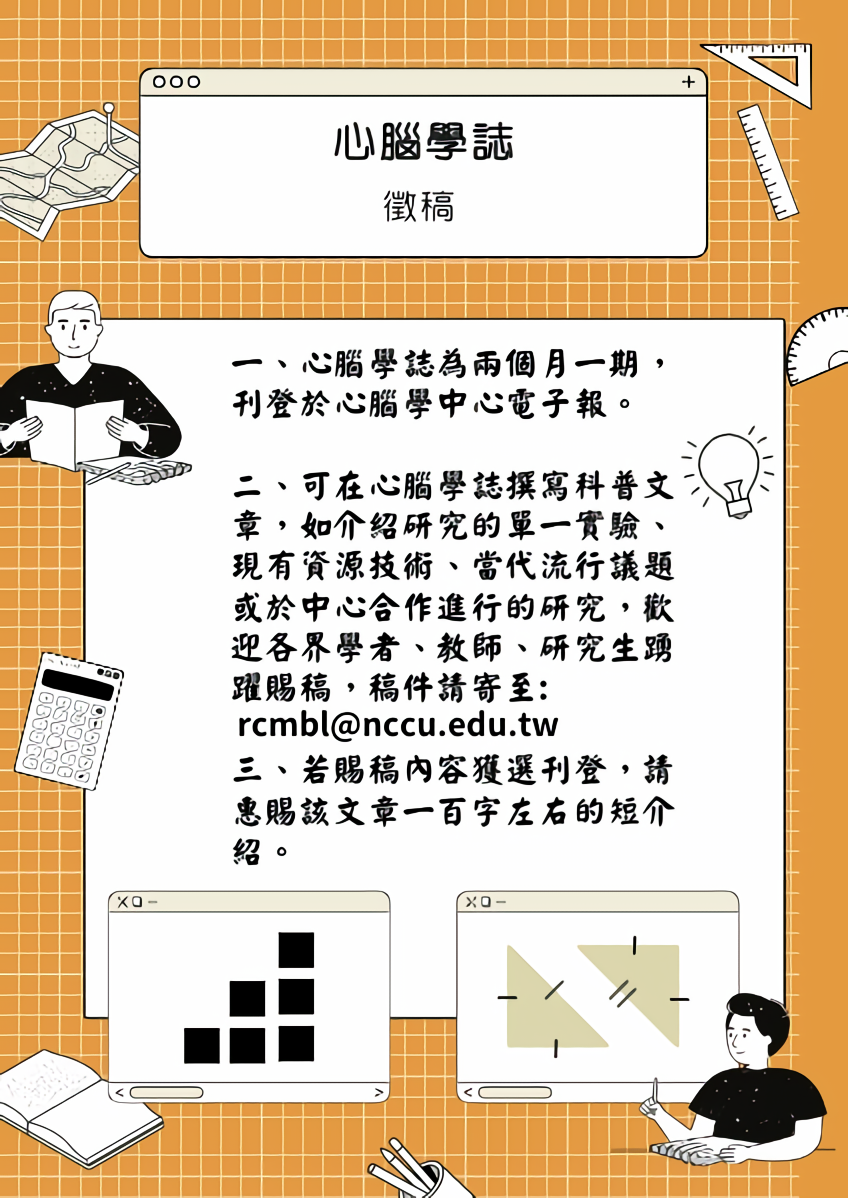2025-06-11
記憶的節律點——呼吸
2023第一屆「心智與腦科學」 - 心理、神經、與大腦 科普寫作徵文 A組心智與腦科學-佳作:陽明交通郭O華
試著深吸一口氣,想像充沛的氧氣進入到血液中,你的血液在加速流動,心跳加速,全身充滿力量,此時你正在突破人類的極限,成為與鬼一樣強大的存在。沒錯,這就是颳起一陣旋風的鬼滅之刃中的「全集中呼吸」。雖然只是動漫的虛構世界,但呼吸對於我們而言或許也不僅僅是氣體的循環而已。
過去幾年中,人們逐漸了解睡眠時呼吸狀態對海馬迴記憶固化的影響。而最近,科學家藉由光遺傳學與CatFISH技術(compartment analysis of temporal activity by 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發現暫時呼吸中止與呼吸頻率改變可能影響小鼠清醒時的記憶與認知表現。
呼吸能否影響記憶?我們的記憶竟然由呼吸所控制?2022年1月,一篇發表在Nature Communications的研究裡,科學家提出在睡眠狀態下,呼吸頻率能做為一個規律的訊號(stream of rhythmic)輸入大腦,使得海馬迴記憶固化以及其餘大腦功能正常運作。同年9月,也有科學家提到呼氣與吐氣間的轉換(expiratory-to-inspiratory phase transition)會影響記憶提取(retrieval process)的表現。由此可知,呼吸的節奏與認知功能有著密切的關係,也成為科學家探討大腦功能的另一方向。
為了探討在清醒狀態下呼吸與記憶處理的關聯性,來自日本兵庫醫科大學(Hyogo College of Medicine)的研究小組操作一系列實驗。由於位在延腦呼吸中樞的Pre-Bötzinger Complex是負責產生呼吸訊號的地方,所以被研究小組選為操控呼吸的目標。研究小組利用光遺傳學技術,以腺病毒為載體使光敏感通道蛋白(channelrhodopsin-2 , ChR2)表現於Pre-Bötzinger Complex區域。由於ChR2是陽離子通道蛋白,在照射藍光活化後,會使陽離子進入神經細胞發生去極化進而產生動作電位(圖一)。因此藉由照射藍光,可以使該區域抑制性神經元(inhibitory neurons)活化並抑制興奮性神經元(inhibitory neurons)來干擾呼吸訊號的產生,使呼吸頻率降低或暫時性呼吸中止(apnea),進而達到操控小鼠呼吸頻率的目的。同時,研究小組引入CatFISH技術,以螢光標定的方式,尋找海馬迴中處理記憶相關區域(CA3)的超早期基因(Immediate-early gene, IEG)的mRNA,由於該類基因的mRNA在神經細胞接收到外界訊號後會立即表現,因此該mRNA在細胞各區的含量可為判斷特定區域活化的指標。
利用上述技術,研究小組針對小鼠設計了兩項實驗探討對於記憶登錄(memory encoding)的影響。首先,在實驗操縱組的部分,研究小組使小鼠的Pre-Bötzinger Complex區域表現光敏感通道蛋白,讓其呼吸狀況可被藍光調控。在第一個實驗裡(圖二),因為小鼠對於新事物有較多好奇心,而較容易厭倦舊物,所以研究小組於實驗空間中擺放兩相同物品在小鼠面前讓其熟悉並在小鼠靠近物體時施予連續藍光照射,誘發暫時性呼吸中止。而間隔20分鐘後小鼠再次進入實驗空間時,他們將物品換成一件舊物與一件新物,觀察小鼠是否正常表現出對於舊物的厭倦(discrimination)。同時,研究小組也設計與恐怖記憶和迴避學習有關的實驗(圖三),他們將小鼠置於壓克力箱中,透過背景色的明暗與背景音的高低作為提示實施腿部電擊(footshock)並給予連續藍光或間歇性藍光,分別對操縱組小鼠造成暫時性呼吸中止與呼吸頻率的改變。在間隔24小時後再次進行相同的實驗,觀察小鼠是否能夠記得甚麼背景色與音高的環境會遭受電擊並因此降低其行動力,來判斷小鼠記憶登錄的表現。
透過上述實驗,研究小組得到重要的結論。在物件辨認實驗中,操縱組,即受光遺傳學技術操縱的小鼠,在連續光照誘發暫時呼吸中止時相較於對照組,即正常小鼠,無表現出對舊物的厭倦與新物的偏好。此外在電擊實驗中,操縱組的小鼠在連續光照下相較於對照組無法表現出對於會實施電擊的背景條件(白牆與高音)下行動力的下降。以上兩組實驗皆表明操縱組的記憶登錄功能在受藍光照射誘發之呼吸中止時明顯下降。而研究小組也用CatFISH技術來觀察腿部電擊實驗的結果。在過往的研究中發現,IEG基因中的Arc基因的表現在未活化或已活化中的突觸較剛受刺激的突觸高,而在實驗結果中,可以發現Arc基因在操縱組中的表現量較高,符合觀察結果(圖四)。另外,研究小組除了以連續藍光照射,也利用不連續藍光來干擾小鼠的呼吸節奏,並觀察影響。在電擊實驗中,若以10赫茲照射藍光,操縱組小鼠在呼吸頻率上會受些許干擾,但卻有更優異的記憶表現;而若以4赫茲的頻率照射小鼠,操縱組小鼠的呼吸頻率會明顯下降,在記憶登錄表現上也有顯著的降低。
由此可以推論,連續光照誘發的暫時呼吸中止與4赫茲光照誘發的呼吸頻率瞬間下降會使記憶能力下降,而10赫茲光照誘發的呼吸頻率略為改變卻會使記憶能力提升。然而,如同研究小組所說,實驗的結果與原理仍需更多深入的了解,例如:小鼠海馬迴記憶收錄的功能是因呼吸訊號的改變而受影響,還是因呼吸中止造成心跳與血壓改變造成的等等,而呼吸訊號的改變如何影響記憶乃至於整體大腦的運作過程也仍有許多未解之處。即便如此,這樣的發現仍然為呼吸頻率與海馬迴記憶收錄過程的相關性提供了良好的實驗舉證。結合先前的關於睡眠與清醒時呼吸與記憶相關的研究,可以更加確認的是,呼吸會顯著影響人們的記憶處理歷程,從收錄、固化到提取,每個層面都可能受到影響。若能更加深入探討呼吸狀態與記憶歷程,或許能夠提供未來在阿茲海默症等失智症相關的治療以及認知功能的訓練,前景可期。
呼吸是氣體的循環,生命的流動,也可能是記憶的幫浦。當期末考來臨時,也許備感焦慮,不妨靜下心觀察呼吸,試著體會這深不可測的魔力。
參考資料
原始論文
Emiliani, V., Entcheva, E., Hedrich, R. et al. Optogenetics for light control of biological systems. Nat Rev Methods Primers 2, 55 (2022).
Karalis, N., Sirota, A. Breathing coordinates cortico-hippocampal dynamics in mice during offline states. Nat Commun 13, 467 (2022).
Nakamura, N. H., Fukunaga, M., Yamamoto, T., Sadato, N. & Oku, Y. Respiration-timing-dependent changes in activation of neural substrates during cognitive processes. Cereb. Cortex Commun. 3, tgac038 (2022).
Nakamura, N.H., Furue, H., Kobayashi, K. et al. Hippocampal ensemble dynamics and memory performance are modulated by respiration during encoding. Nat Commun 14, 4391 (2023).
Okuno, H. et al. Inverse synaptic tagging of inactive synapses via dynamic interaction of Arc/Arg3.1 with CaMKIIβ. Cell 149, 886–898 (2012).
新聞
John Nosta(2023),Psychology Today: The vital breath of memory
https://www.psychologytoday.com/za/blog/the-digital-self/202308/the-vital-breath-of-memory
圖片來源:
圖(一): Emiliani, V., Entcheva, E., Hedrich, R. et al. Optogenetics for light control of biological systems. Nat Rev Methods Primers 2, 55 (2022).
圖(二)、圖(三)、圖(四):Nakamura, N.H., Furue, H., Kobayashi, K. et al. Hippocampal ensemble dynamics and memory performance are modulated by respiration during encoding. Nat Commun 14, 4391 (2023).
其他相關連結
CatFISH. Immediate early gene imaging with catFISH. Fluorescent in situ... | Download Scientific Diagram (researchgate.net)
IEG. Immediate early gene - Wikipedia